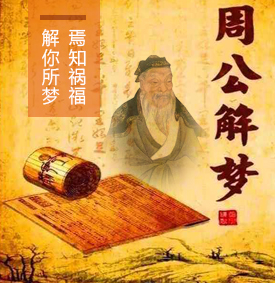怀念有天哥
张有芷
2006年9月30日中午,从嫂嫂来的电话中得知哥突然去世的消息,当时真是难以让人相信、难以接受这一严酷的事实。几天之前,我还与哥通过电话的,他在电话中说近来身体还好。本打算国庆节后去北京看哥的,没想到却留下了终生的遗憾!
哥在2005年患病后,我曾探望过他两次。一次是在2005年3月,哥在北京宣武医院住院治疗。我来之前,新中弟已经陪伴哥十几天了。另一次是在同年10月,哥早已出院,在家休养。病情得到控制,康复良好,活动基本自如,但体力欠佳,易累。使我后悔的是,这两次探望,都没能做到尽心尽力。我后悔哥在住院时,没有陪伴到他出院,本应一直等到嫂嫂好朋友的女儿王女士来到哥家。就算我家有事要提前返汉,也应请新中弟再来北京。因新中说过,需要他的话,他再来。我后悔10月那次与哥见面,在哥家只待了一天半,何况当时嫂嫂身体欠佳。哥叫我多留几天,嫂也劝我多陪哥几天。而我却因有其他事先约好的事,没能留下。回武汉完成了这些事后,又没再去京探望哥,以致这次与哥见面是最后的见面。回想起来真后悔莫及!常常心中感到无比遗憾和愧疚!
哥比我大6岁,我读小学时,他已读中学了。抗战胜利后,我们家从兰州回到武汉,哥去了南京。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南京名校??金陵中学。哥住校就读,直到他高中毕业。这期间,我们家从武汉回到老家滁县,又从滁县迁到南京。哥因住校,只有寒暑假才能和我们在一起。在南京时,他星期日有时回家。1950年哥考上大学后,很少回家。1955年,哥大学毕业工作以后,就更少回家了。1957年,哥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后,在一人遭殃、株连九族的极左路线下,他生怕影响我们,从不与我们联系。即使偶尔见面,他也是沉默寡言,性格发生了很大变化。实际上,他就是不与我们联系,这条极左的路线也不会因此而改变。他遭遇打击的二十年间,我真不知他是怎么熬过来的。
我小时体弱多病,记忆力差,能记得的往事不多。早期和哥在一起时,他很少谈论他自己,我也不敢多问;因此对哥的了解较少,对其内心世界更是知之甚少。后来惊喜地获知哥被评为1976年吉林省先进科技工作者、出席了1978吉林省科学大会并调回了北京水科院。此时的哥,不仅已是吉林省的名人,而且在整个水利界也小有名气了。近几年,从哥的专著、嫂嫂寄来的材料及他的同行们对他的评价中,才知道我的哥是一个有坚定理想、有追求、有抱负的一位高尚的脱离了低级趣味、为国家为人民做出巨大贡献的好哥哥。
活泼、顽皮、聪明的男孩
小时候,在我的印象里,哥是个性格开朗、活泼、调皮并十分聪明的男孩。在兰州期间,我曾和他睡一张床。哥要早早起来去上学,而我可一直睡到太阳照在床上。有一天,我醒来时,发现我床头有一只猫,把我吓了一跳!原来是哥放的。
他没事时和我一起玩,用手弹我的手肘部,有非常酸麻的感觉。他说这部位有一根麻筋,弹上去就会酸麻。
哥还教我用手来吹口哨,用弹弓打麻雀等等。可见,当时他是很顽皮的。
父母对哥的教育抓得很紧,专门请了国文老师强化他的国文学习。每周规定背诵老师指定的古文,背不出,就罚跪。哥很少被罚,常能背诵,所以哥的国文基础相当好。
抗日战争胜利后,我家从兰州迁到武汉。哥在南京读书。 暑假才能回家。我们家住武昌,家附近有座小山,哥常带我上山玩。山上有一种小草,哥说这草的心可以吃,他拔了一些吃,也给我吃,真的,它的汁是甜甜的。
1948年我们回到老家滁县。住在伯父家的大宅子里。这是座老宅,比较旧,有好几进,共有几十间房间。有的房间没有天花板,有些潮湿,梁和撑梁的柱子都是全木的。暑假的一天,我和哥在这儿玩,哥赤膊站在蹬子上往柱子上挂东西。突然,一条花蛇从屋顶上掉下来,恰巧沿着哥的脊背滑下,我吓得哭了起来,而哥却十分沉着,一点没有怕意。我求他快把蛇打死,哥说这是家蛇,不能打。可见当时他已有保护生态的意识了。
在滁县我们没住多久就全家搬迁到南京,住在宁海路58号。这是一座二层的楼房,后有一个大院子,楼房旁还有汽车间和几间平房。据说这房子的主人已逃往台湾,管理人怕房子被共产党没收,而让我们免费暂住。哥只有在暑假和星期天才回家住。哥单住一间,他房子里挂了许多他画的画,哥经常在阳台上锻炼身体。听妈说,哥的学习成绩非常好。这期间,爸爸在北京工作,家里两个弟弟还小,哥就成了我家唯一的男子汉。我们住的房子太大,空荡荡的,到了夜晚,只要哥在家,他就要把各房间巡查一遍,关好大门,好让妈妈安心睡觉。
哥就读的金陵中学环境优美。有一次哥对我说,你到我们学校来玩玩,看看我们学校,我请你吃冰琪淋。于是 一个星期六下午,我带着新中弟一起来到哥的学校,哥带着我们参观。给我的感受是,这所学校真大!真美!哥带我们参观学校的目的也许是要我好好学习,将来考上好中学。
1950年哥考上了大学,此后,我和哥在一起的时间就很少了。
孝敬父母,关爱弟妹
哥是一个孝子、常为别人操心的人。
在兰州时,哥放学回家,总是首先向母亲报到。一天,母亲在躺椅上闭目养神。哥放学回到家,走到母亲身边,本想叫妈的,看到她闭着眼睛,仔细叮着妈妈看,发现妈妈真的睡着了,怕吵醒她,他才轻轻地走开。
在滁县时,只有在寒暑假,哥才回家。所以母亲在伙食上对他特别关照一些。暑假的一天,我们在院子里吃晚饭,母亲给哥一个咸鸭蛋,而她自己没有。看到此情景,哥哥一定要把这鸭蛋省给妈妈吃。两人推来推去,直到妈妈发脾气说,你再不吃,我就要扔到墙那边去!哥见妈妈生气了,才把鸭蛋拿到自己面前。此时妈妈笑了。
1950年夏,哥高中毕业,考取了清华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。他选择了哈工大。一年后他回南京过暑假,整个假期都未与中学同学聚会,和我们也很少说话,成天待在家里埋头翻译《斯大林文化宫》。当时我认为哥是为了学好俄文。直到2007年秋,我在南京才听大中弟说,哥在入大学时,父亲是借钱给哥作路费的,哥是为了还钱才去挣稿费的。翻译稿费约100多元, 40元还债,剩余的大部分丢给了家用。哥真有志气而且用心良苦!
哥读大学后不久,母亲就因患癌症不能再去上班了(母亲原在陶行知师范附小教书)。家里经济也开始吃紧。哥在哈尔滨读书,离家太远,不可能每个假期都回家。在母亲病重已不能起床的1953 年夏天,哥回家看望母亲,他成天坐在母亲床边一张方桌旁看书,守候着,从不外出,也不会见同学、朋友。每次我们给母亲换床单时,哥就把母亲抱起来,等我们换好后,再把她轻轻地放回去。这年9月,母亲就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母亲去世后,我们一家6口全靠父亲一人工资生活,显然经济上面临极大压力。我读初中时已交不起学费,不得不向校方申请减免学费,并申请助学金,在学校免费用中餐。哥大学毕业,就立即把每月大半工资往家寄。他被错划为“右派”后,嫂嫂每月往家寄钱,从未间断过,直到我和新中弟大学毕业,走上工作岗位。我们能有今天,除了父母的养育之恩外,哥嫂功不可没!
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,我们家从安徽到湖南到兰州再到湖北、安徽、江苏,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,我几乎没有好好读书,加上我从小体弱多病,小学学习成绩很差,小学勉强毕业。小学毕业时,哥曾对我说,你一定要好好学习,将来长大要出去工作,千万不要成为只会围着灶台转的人。高中毕业考大学填写志愿时,哥建议我学气象学。我按他的建议,考上了南京大学气象系。大学毕业后,走上了工作岗位,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职业妇女。这和哥从小对我的启迪和关爱不无关系。
我读高中时,新中弟读初中,他和我同校。新中弟喜欢画画,哥哥知道后非常支持,汇款来帮助购置画笔、纸和油彩等绘画用品,培养他并创造条件发挥他的绘画才能。由于有了这些有利条件,在老师的指导下,新中弟在初中时画的画,参加了南京市少儿画展,并获奖。后来,新中弟的画还被选送到国外展览。
虽说我和哥在一起的时间很少,但每次见面都是非常开心,每次分别都是依依不舍。哥每次来汉出差,都要抽时间来看我,每次我去北京看他,他都要把我送到汽车站甚至火车站。
有一次,哥来武汉出差,带来一大捆小人书,给我两个在小学读书的女儿看。这堆书足有5斤重以上,从那么远带来,真够累的。我把它们藏在床下,两小女表现好时,就拿出两本给予奖励。这事在我两个女儿的记忆中,非常深刻。
还有一次,哥来武汉,带来北京新鲜柿子,也是挺重的。武汉没这种柿子卖。他就是这么一个总关心着我们的好哥哥。
1999年嫂生病住院,我去北京看望她。哥一定要到火车站来接我,我对他说,嫂嫂住院,你一人够累的,千万不要来接我,我能找到你家的。而哥说,这几年北京变化大,你会不认识路的,我一定要接你,并叮咛说下车后怎么出站,他在什么地方等我等等。下了火车后,按哥指定的方向出站。我一眼就看到哥站在那里盯着出站的人群,我心里一振,这么早,你何必来接我啊!我们一起到了哥家,他还在前一天专门为我烧了红烧肉。一周后,我返回武汉时,哥又要送我去火车站。我说,去车站的路我已认识了,你这么辛苦,不要送了。可是哥坚持要送,他一直把我送到进站口,才回转。哥生怕我有什么不顺。
从哥家到火车站,我即使乘出租车去火车站,哥也要送,说你是外地人,司机也许会绕路开,多收费的。哥就是这样一个总爱为别人操心的人。
哥不仅对我如此,对弟弟也是这样。每想起这,内心愧疚啊!我为哥哥做得太少了!
铁铸的骨头
2005年3月,我在北京宣武医院陪伴哥几天。每天下午,陪哥去康复中心进行康复训练。从住院部到康复中心,要经过一个小花园。哥要在园子里坐一会,晒晒太阳。也许是在病房里待得太久,到了户外,感到空气特别清新,哥的精神好了许多,话也变得多了起来。谈到他希望与黄委会同志去黄河上游考察;谈到世界银行请他审查某个项目的情形;谈到水科院领导对他的关怀,退休后一直回聘他,并给他的回聘费是在当时也是两个最高的之一;谈到台湾方面邀请他去台湾讲学:谈到曾为同事争取住房等等。哥谈了许多许多。有一次他说:“一个同事说,我的骨头是铁打的,他这样评价我,我感到惭愧啊!如果我的骨头真是那么硬的话,我就活不到今天了”。说到这,他沉默了。我说,是啊!在极左路线统治中国的年代里,不少品学兼优的学生、有成就的知识分子、老党员、老干部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、反革命分子、反党分子、右派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莫须有的罪名。他们这些好干部、好领导、好同志遭到无情打击 ,有的被活活整死,而且死得很惨。为新中国立下了赫赫战功的彭德坏元帅,就是因为骨头太硬,才遭到无情打击,含怨而死!
哥的同事说他骨头硬,我想意思是指他有坚定的信念,在逆境中具有坚忍不拔的大无畏精神, 虽遭遇非人待遇,仍能挺直腰杆,正确对待自己,对待环境,顽强地活下来,并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机会为人民、为社会做贡献。
说哥骨头硬,意思也是指他为人正直,心怀坦荡、对工作一丝不苟,能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,不受外界影响。记得有一次哥从三峡工地来武汉我家,说在三峡工地审查某项目时,他发现了施工中存在的问题。在场的领导和专家起先未重视,但后来还是接收了建议,修改了施工方案。
哥说他感到惭愧,我想意思是,在他的头脑里,“硬骨头”的标准很高。他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,但是目前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。哥对他遭到迫害的、人生最宝贵、最能做出成绩的20年的青春年华,还是感到遗憾。如他在《水利情》中所述:“我很羡慕那些比我年长的学者,他们被打成右派、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时已经成长为大树,风暴一过照样郁郁葱葱。我当右派时才24岁,在学术上还是一株幼苗,如何能经受20年的狂风骤雨的摧残”。这20年是人生最有活力、精力最旺盛、最富有创造力的20年!在哥被平反后,特别是改革开放后,哥重新回到了水科院。年已45岁的哥,离退休年龄只有15年时间。他全力投入到水利事业中,做“生命最后的一次冲刺”。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,以夺回失去的20年,去完成这20年本可做的而又未能做的工作,为国家、为社会、为人民献出自己还剩余的光和热。哥的后半生,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大量工作。仅从他同事写的缅怀哥的纪念文章中得知,哥主持、参加完成了大量设计、施工、科研工作。到过近30余座水利工程工地。凭着他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,解决了诸多设计和施工中的技术难题,为国家节省了数亿元资金;发表论文100多篇、专著二部、合著三部、译著二部;获全国科学大会重大贡献者奖,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、三等奖1项,吉林省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3项,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、二等奖4项、三等奖2项,大禹二等奖2项等诸多奖项;作为博士生导师,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人才。水利界同行们称他为“水利巨匠”、“一代大师”、“把自己还剩余的光和热,全部献给他所挚爱的水利事业”。哥为水利事业做了这么多贡献,直到他临终前还认为自己做得不够,尚没有达到他对自己要求的标准。
未能完成第三本著作
哥进入古稀之年后,打算写三部专著。完成第二本著作时,不幸患上了脑梗阻病,被及时送进北京宣武医院抢救。医生对他进行了全面检查,有针对性地给予治疗,用药也经过慎重考虑, 在治疗脑梗阻的同时,采取不影响心脏的治疗方案。经过打吊针、吃药和康复训练,恢复得很快,从不能起床到可以独立行走,日常生活基本能自理。半年后,我见到他时,看他气色很好,虽还有点后遗症,左手不大灵活,但行动基本自如,还能上街买菜,真为他高兴!
一天,我陪哥去宣武医院复查,我问哥,你在发病前有没有什么先兆?哥说有。我又问,你有什么表现呢?哥说最明显的是耳鸣。我问,你去看医生了吗?哥说,看了,花了100元挂了个专家号,专家只开了些药,我就回家了。哥还说,当时要做进一步检查,吊点滴就好了。我当时感到太遗憾了。因为我在医院B超室门口的宣传栏上,就看到脑梗阻发病的先兆等等表现的宣读资料 。哥发病前有耳鸣等现象实在太典型了!难道这位医学专家不知道吗?为什么不为哥做进一步检查?由于医生的不认真、负责,致使哥得了本来可以避免的病,受了许多痛苦,也耽误了许多用以写第三本著作的宝贵时间。
2006年9月初,哥正着手撰写第三本著作《隧洞工程的科学与技术》时,出现了脑供氧不足的反映。嫂嫂及时把哥送进医院检查和治疗。哥在医院住了20天,医生根据哥的身体状况尚好,症状有所改善,同意出院。可是,哥才出院不到两天,就离开了人世。难道医院对此不应负有责任吗?哥在医院20多天的时间里,医生没有给哥进行全面检查吗?哥有心脏房颤的毛病,就没引起医生的关注?
如果医生医术精湛一些,对病人真正负责的话,哥不应这时就离开人世。他的第三部专著是可以完成的。
水利人心中的大师和楷模
哥是2006年9月30日中午突然去世的。 丧事定于10月4日,哥的女儿从美国回来后办理。嫂嫂本打算一切从简,是结构所的同事们坚持要安排向遗体告别仪式。由于哥是突然去世的,又恰逢“十一”黄金周,人们忙于外出度假,很多同志不知哥去世,估计参加告别仪式的同志不会很多。
10月4日上午8时,我们家属来到北京八宝山殡仪馆灵堂时,没料到已有许多哥的生前好友、同事早已来到。水科院的同志把灵堂布置得庄严肃穆 ,哥被安放在苍松翠柏和鲜花之中。灵堂周围已放满了单位、领导、同事和亲友们送的花圈。不少花圈的挽联上,有对哥一生的简短评价。例如,原水科院张泽祯院长的挽联上写着:“处逆境,冷对厄运,不失为英雄本色。逢盛世,意气风发,铸造就博学伟业”。
北京以外的不少单位闻讯后也纷纷发来唁电、唁函。据不完全统计,来向哥告别的同志有200多人,除了哥的生前好友外,水科院新老领、工程院院士等也来吊唁。 来唁电的单位有20多个。电文中表达了水利界同人从内心表示对哥的去世的挽惜之情,对哥一生的贡献和崇高品德的肯定。人们称他为:“水工建设的巨匠”;“一代大师”;“为中国的水利事业呕心沥血、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,树立了水利科技工作者的光辉榜样”等等。
哥虽然离我们而去,但他为水利事业做出的贡献和他的精神永存!“学高为师,德高为范”。他不仅活在我们心中,也永远活在水利人们的心中!
![]() 作者简介:张有芷 原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
作者简介:张有芷 原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